
追"是否删除此人好友?""是。"删除你微信的那个下午,我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划清了界限。同时把自己的微信名改成了一个字。追。追逐某个人的影子,而后归去。我看了一眼你的微信签名: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倾诉。_追忆,亦或追逐。苹风吹颂着去日的故梦,飞瓣乱扬成雨,记忆,是折损了的玉璧上四散而落的华晶,一并吟唱起了怀金悼玉的悲歌。我于是伸出手,探向梦中婀娜曼妙的倩影,四面八方无数刺耳声音涌来,浑身上下都被兜头浇上的脏污浸染彻底。唯独那一张脸,依旧是记忆中凛凛而开的澄澈模样。"因为你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学生啊。”你知道么,我是喜欢你的。这秘密,或许他知,我知,众人知,而你,却故作不知。喜欢你的才情放逸,风光霁月,沉静博雅。开口便是三春桂子,十里荷花,亭台楼肆,烟柳画桥;喜欢你明眸善睐,好似会一套微妙的哑语,"水似眼波横,”轻轻一笑,就落了桃花似的婉转多情,温暖可爱;喜欢你的博闻强记,语调轻缓而又铿锵,有如林间之白鹿。你的名字里有个婧,你也的确是个娴静的人,让我想到《诗经。静女》当中的"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你是个美好的人。你说再好的白璧也有微瑕,在迷雾中看花的人总不容易被蔷薇刺痛手臂。从小到大头次见到这样博学多闻的老师,彼时十四五岁的小少女只好偷偷的看,偷偷的仰慕。面上尽管仍是默默的,心头却升起从未有过的,朦胧的、皎洁的欢喜,像是羽翼未丰的雏燕归来,剪破一池春水,久已冰封的湖面漾起层层涟漪,最后却给在檐的倒影下抹去了,轻轻的。那是四年前一个再遥远不过的下午,遥远到不曾记起的下午,那时候的你没有孩子,尚没有家室的束缚,那时候的我单纯可爱不谙世事,顾盼鲜艳,情致两饶,既是明媚鲜艳的女孩子,也是先生最爱的女学生。槐序时节三分凉意袭人,窗户外是初春的枝,你给我们讲《岳阳楼记》,讲《滕王阁序》,你于讲台旁踱步,清明的光漏过窗帘,吻你光洁的额,你略施粉黛,空凭一段年轻的惊艳,折煞这花信般的年。我忘不掉,我怎么可能忘得掉呢。怎么可能呢。我喜欢听你读周记,读作文,因为那里面总有我的一份,看你袅袅婷婷的走到我的桌前,纤细美丽的食指轻轻叩着桌面,就宛如…悄声的爱抚。然后你走过,留下清和的香气。我本以为删除了微信就能够与我的过去划清了界限,可是喜欢一个人,你会发现,这世界的处处都是她留下的痕迹。你送的毛绒大猴子孤零零的躺在大床上,嘴角带着有些落寞的微笑,像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你曾在这里夹着一张纸条,你说我看见这猴子仿佛看见你一样,于是在(于是在)中专里无数个被泪水和嘲笑浸透的夜里,我看着它,抱起它,就有了继续努力的勇气。你从前批改过的本子我也没有扔掉,上面画着大大的笑脸,写着鲜红的A+。从前获得过的奖状,它们泛了黄,破了页,但他们时时刻刻在提醒着我,我有怎样明媚的,灿烂的过去。我才发现其实我从未真正堕落,我未曾沾上烟酒,甚至不爱说粗话。我所有的懒惰都是因为过去所造成的疲惫,在我即将堕入深渊的时候,也总有一双柔弱又坚韧的手,将我自泥潭中拉出。"不能这样。"她对我说的轻轻,就好像在劝解一个误入歧途的孩子一般。孩子,是的,我多么希望,自己永远是那个她最爱的女学生,她最爱的女孩子,那个总是出口成章,乐观上进能让她自豪的弯着眼笑的女孩子。她唤起我的自尊,留给我内心最后一片圣洁之处。我喜欢写作,也喜欢你。可惜,你不会听到了。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倾诉。—“她真恶心,算我瞎了眼,看错人了。”一位初中的陈姓同学说。“你确定是她么?”一个男生的声音。“她怎么堕落到这个地步呢。”“我就知道她会来这里。”“嘁。”……希望,绝望,希望。嘲笑声犹在耳畔,振聋发聩。我知道,从前的事情不会忘记,只是想不起来而已;我知道,将自己从内部狠狠剖开,然后把自己的左手按在心脏上听它挣扎的感觉,是疼。就像是从不结痂的伤口划再次被薄薄刀片锋利的棱角划开。冰冷的感觉顺着血管流过我的脊背往上爬动,最后传递到我的心脏,不过一瞬就冻结成冰,血为之不流。疼,疼得火辣辣的,但绝对不是这种疼法——那真是打进骨髓直接捅进了我的脑子里,钻心蚀骨,回忆化作一把刀子,一片片将人凌迟。喊出来吧,这样就不疼了。我这样告诉自己,可是我无法阻止自己不去回忆,不去思考,不去遐想,过去越是鲜明,亮丽,纯净,跌落到另一个世界的时候就有多少黑暗、冰冷、残忍。我疼。我不记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讨厌那个教英语的周姓老师的,尽管我以前也曾真心的仰慕过她,就像我曾经也天真的仰慕过你一样。也曾偷偷的用稚嫩的笔触写下赞美她的文章。还曾得到(曾得到)你的夸奖。谁曾想,这会是日后他人嘲笑我的话柄。初二那年,学业压力陡然增大,她突然变得愈加严厉苛责起来,原来和蔼可亲的笑容也不见了,不得不承认她的变化很大,在当时的我的眼睛里,她素来是个眼眸弯弯,笑容和蔼的人啊,怎么一夕之间变作了这副模样,实在令我难以理解。我们成绩稍有下降,她便劈头盖脸的斥责,丝毫不留情面,让我感到压力、害怕和愤怒。默写,试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更令我难受的是,她对待好学生和后进生的差别愈加明显,考得好依旧风平浪静,考得不理想,原本慈眉善目的面容就开始挤作一团,由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奶奶变为一个面目狰狞的女巫,覆雨翻云,实施“暴政”,变化不可谓之不快。她把随堂默写的分数作为晚上抄几遍单词的标准,为了晚上能少抄一些,除了班上几个英语成绩拔尖的同学,其他的同学或多或少都在偷偷的作弊。我原本的英语成绩虽然不算拔尖,但也不是最弱,大约是十多名的水准,因此她对我的态度时好时坏。但是自从她这样做过后,我对她的反感与日俱增,我的英语成绩也一落千丈,再也无心学习。从最初的120多分一直下降到在及格线堪堪徘徊,原本就惨绝人寰的理科则彻彻底底崩溃下来,可谓是“疑是银河落九天。”“你最近到底都在想些什么,你太令我失望了!”我垂下眼眸,用一个少年人无关紧要的倔强来回应她,我能不看她的脸就猜出她的脸上有几分竭力抑制的愤怒:“和我出来一下。”“你最近究竟是怎么了,你看看你这成绩,原来考成什么样,现在又考成什么样?”……她的话我没有听进去,我也不想和她解释自己考差的缘由,只有少年主观片面的情绪化的愤怒占据了我的整个额叶。然而这还不是真正的导火索,真正的导火索是在我们又一次默写成绩糟糕之后她把无辜的班长送来的作业本一股脑全丢在地上,然后迁怒于班长(于班长),发了一通有史以来最大的火:“批批批,批什么批,不批了!!!”声音大到充满了整个教学楼,然后她站在讲台上板着脸,课也不再讲了。那一刻她真的像极了狰狞的女巫。那一刻,过去的她的形象在我眼中彻底破碎。我看到班长的眼圈红了。但她还是非常克制的,把作业本整理成一堆。然后站起来的是素日袒护她的程,一个高高大大的男生。班里谁都知道班长从小没有父亲。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不知道为什么,那一瞬间十四岁的我突然恨极了她,那是一种从胃里翻涌出来的恶心,一直以来对她的意见在一瞬间爆发,素日敏感内向的我就这样站起来,反问:“为什么?婷没有错!”为什么?为什么要变成这样?我多想直视她的眼睛问问她,当时的她。沉默,可怕的沉默。后来,她平静下来以后,和婷道了歉。又恢复到从前笑眯眯的样子了。只是她在我心中的印象,已经大打折扣。如果你稍微研究过青少年时期的心理,你就应该知道青少年是个矛盾体,他们举动的动机是渴望得到成年人的关注和问询,他们心思单纯,未经过过多的教育的开化,所以更应该加强引导,不分青红皂白的压制会让他们身心压抑,更可怕的是他们因为未成年,还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导向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这个年龄是相当危险的,敏感和早慧,幼稚与成熟交杂在一起,他们的自信、价值观通过成年人而建立,他们敏感,心智薄弱,成年人的言行举止对他们而言是信条一样的存在,高尚与卑琐,诚信与谎言,成人世界的教条由他们来制定,再由教师的口传到学生们的心中,形成对这个世界最基础的认知,可以说教师在这个年龄段的重要性等同于父母。这个特性在某些调皮的男生身上更为突出,正因为这样,他们更容易得到老师的关注,从而避免很多事件的发生,可是,女生呢?大众对于女生的认知通常是文静的(文静的),乖巧的,省心的,她们每天夹着干干净净的作业本讨老师的开心,可是她们的另外一面是敏感且含蓄的,心思也是内敛的,这使得她们的内心如雨雾朦胧的烟锁重楼,若非走近,绝不会看得真真切切。如果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平凡的,敏感的,单纯的仰慕着老师的偏科的女孩呢?那就更不会受到她的关注。那时我的含苞待放的敏感和早慧让我更早的看透了她的另一面的某一角,我却很难理解她为什么要那么做,毕竟让一个14岁的初中生去剖析多面复杂的人性,这太难了。所以当时的我只是愤怒,因为阅历的缺乏,我不了解,我不明白。于是我(于是我)开始故意试图引起她的注意,又或许是出于对她行为的不满,我开始做我过去那些没有做过的事。我和周围的人一样,一起作弊,并且在她愤怒的时候得到一种近乎报复的快感,只是我不知道,这个时候的我,也展现了人性恶的那一面。我开始给她起各种难听的绰号,在数学课上开小差,写纸条。她让一个英语成绩比我差的人辅导我默写……那一段日子,我好像什么都心不在焉,什么都不在乎,我好像彻底底的堕落成了我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好像我真的变作一个废物。真的是这样么?前桌陈姓男生的话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你除了会语文还会什么。”他用两个鼻孔瞪着我,眼神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写了两个字:恶心。他不会了解我看到了周姓老师怎么样的一面,而那个时候仅仅才14岁的我,面对依旧懵懂,成绩优异而又饱受关注的他,我该怎么样向他解释人性双面的复杂与深邃?他是不会看到这一切的。优等生和偏科生的世界不一样,他们单纯明朗得多。而这个时候,更大的打击来了。那个时候甚至没有人,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毫无防备的堕落到了一个极暗极暗的世界,而这并非我所愿,却让我彻彻底底的背上了骂名。——明明父亲是上海人的我,却因为父亲年纪大了早就错过了登记户口的时间,因为政策也因为成绩的原因,我不得不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全国部。甚至,我还没来得及和众人解释甚至是道别,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和今天一样下着雨,14岁的我背着浅蓝色小熊书包,将自己的座位挪到了教室的最后一排。我听到众人的指指点点,他们都以为,我不愿意读书了,他们都以为我就这样义无反顾的堕落,自作自受,心甘情愿。真的是这样吗?我不断问我自己。可我听不到答案。我走的那一天,窗外的树梢还盛着水。宽阔的树叶上掉了串水珠儿下来,打在了湿软的泥里,又好像打在了我的眼上,冰冰凉凉的,没有声响,可我怎么都哭不出来。我只能只把泪给压下去,压到泥里去。接我去全国部的袁老师(袁老师)站在门口等我,他穿得很体面,顺滑的发梳得很齐整,戴着黑框方眼镜(方眼镜),褐黑色的脸,表情晦暗不明。“你要去全国部?”“嗯。”一路无言。两年过去了,这一幕还印在我的脑海里,像黑白胶片电影,在我进入中专的日日夜夜里,反复播放。我没法忘记,我从不能忘记,他们在我入全国部躲避我,像看瘟疫一样躲避我的眼神;我不会忘记,在我进入中专以后受到的种种鄙夷,轻蔑,怜悯,嘲笑,挖苦,或许我的命运,在14岁的那一年就已经注定,我好痛苦,可痛到深处,连哭泣都是那样无力,那样没有资格。天使之战中,恶魔路西法堕落了九个晨昏,由高高的天堂跌落地狱,再无回转的可能。可他毕竟曾有一个天使的名字,叫路西菲尔。属于残酷的另一个世界,在我眼前渐渐打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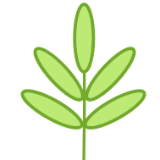
发表评论